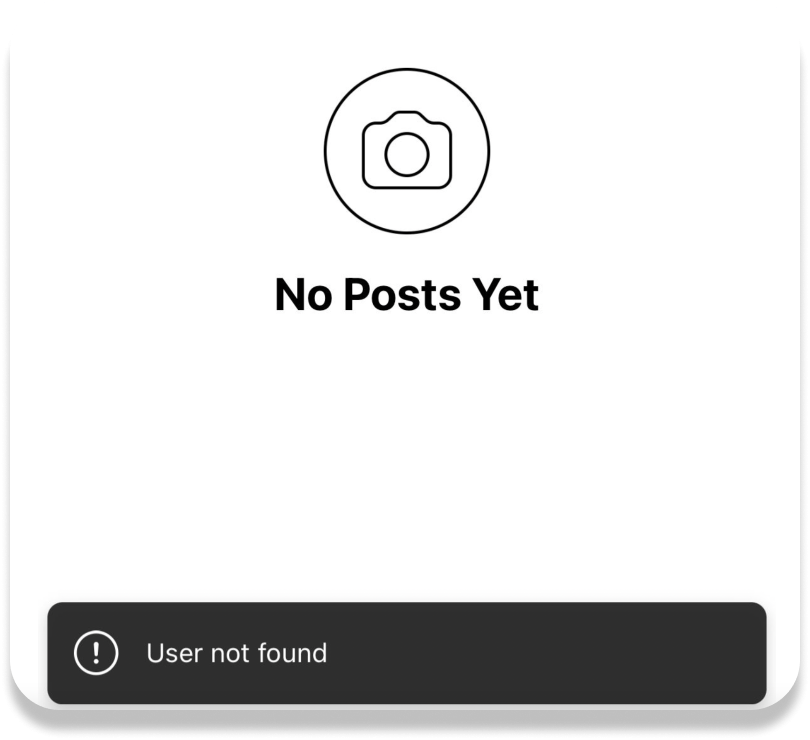我愛 block 朋友!——網絡與社交現象
海中地職人
2024年10月25日
Geneviève 是中學教師,與幾個高中生關係不錯,近來耳聞目睹他們社交上的特別現象。幾名少年的關係,以及他們處理人際關係的手法,具一定代表性,呈現今日網絡發達下,人類社群的特點。
某日是學校陸運會,上述幾名學生邀約 Geneviève 陸運會後吃烤肉,有男有女,為數七名。櫈未坐暖,學生好像成人酒後吐真言,興奮起來,大談同一圈子、關係尚算緊密的餘下一名男生,名叫智強,在他們的圈子中是如何「見人講人話,見鬼講鬼話」,呈雙面人狀。相隔一周,Geneviève 舉行小組活動,參加者就是上回聚會的學生,今回智強也在場。他們閒聊起來,一名男生 Marcus 跟智強說︰「我上星期發現你在 WhatsApp 和 IG block(封鎖)了我,可否 unblock(解封)呢?」智強不慍不火回答,原來早前 Marcus 在 Instagram 發出帖文,透露了他的私隱,他很憤怒,就以封鎖來發洩,至今算是下了心中氣,按理是會解封的。但他同時提出條件,就是 Marcus 能勸服群組內的女同學 Janette 在 Instagram 對他(智強)解除封鎖,他亦會即時對 Marcus 解封。
要多看以上環節一兩遍也不為怪,Geneviève 聽後也思索了一會,向學生問一兩個問題澄清事態,終究理解各方的行為,仍不敢自認理解他們背後的想法。幾名年輕男女的相處方式,可謂反映現在很多人的社交形態,其中兩項鮮明的特點就是︰線上線下舉動不一致,以及行為的意義剝落。
原來朋友冒犯自己,處理的辦法是在線上封鎖他,但面見時言談如故,並不提及受傷害的事。不知所謂「雙面人」,這種在線與離線的差異是否重要特徵。有人說人人在社會上都會戴上面具,否則永遠以真面目示人,許多齷齪事都展露人前,既不符社會規範,個人也生存不了。然而維持一定禮節,不代表刻意虛偽;講真話,不代表不加修飾,再難聽的說話也講盡。又有人說在線上抒發感受無傷大雅,在社交媒體上一個小小動作可換來日常平靜,也不應鞭撻。如果網上抒情有如唱一首歌,也無不可,但舉目可見,會在網上跟朋友 block 來封去的,考究哪則帖文誰看見的,某張照片顯示各人關係如何的,花多少時間和精力漫游網絡,八卦爭論、顧盼自戀。如此本來只充當窄小出氣口的網絡,變成兼職營運的勾當,投放的資源如此多,能說不受它影響生活和心志嗎?本來網絡世界只不過是現實世界的延伸,線上線下不會涇渭分明,出生以來就可上網的一代更不易懷有網上是另一個世界的感受,但他們——以至其他年代的人——的行為線上下卻像精神分裂,如是平日他們以何等精神狀態過活?
所謂封鎖,就是與人區隔,從此對方看不見我的資料,發出的訊息不獲我接收。原來這只是一部手機之內的世界,放下數碼交織的媒介,真人見面時,「封鎖」、「不理睬」、「隔絕溝通」驟然消失。如此這一「block」,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意義。Block 了也可 unblock,即是 do 了可以 undo。Undo 中文譯作「復原」,意即回復原狀,描述的焦點在事物的狀態。英文 undo 的字面意義是「撤消已做的事」,焦點在行為發出與收回。在網上封完又解、跳出跳入就是運用 undo 的功能。朋友相處,話不投機,最多疏遠,或維持泛泛之交。號稱好友,有所齟齬,竟然動用有如絕交的封鎖一招。但原來只要化解冤仇,又可以解封了,所謂封鎖,終究沒有三尺重門,只有紙薄的輕紗,放下就遮掩,揚手則撥開。謂 block 沒有真 block,封完又可以解封,自己明知如此行為沒有意義,也向友儕昭示同樣訊息。習慣這種行事方式,會否誤以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 undo?若認定很多事可以抹去重來,起初的行動又有否意義?如斯下去,就是日復日體驗意義剝落,亦即自行做無數件沒有實質意義的事,就以為世間萬事本無意義,落入虛無之中。
本文絮絮不休談論對網絡和社交的憂慮,其實與網絡本身沒有必然關係,只是這方便的平台令人類既有的自我、既渴望合群又務求出眾的心態變得極端。一如老生常談,工具本來是中性,視乎人如何運用。又再老生常談,人畢竟是群居的,始終有與人建立關係的需要,是否用手機、是否透過社交媒體或通訊程式,只是手法,關鍵還是切實與人相處。對於人類建立社群的未來,既須儆醒,又可懷有希望,否則任何事都不抱寄望,不願動絲毫努力,又會墮入另一種虛無主義之中。
© 本文由作者【海中地職人】創作刊登於Influence In Asia (By HKESE),如未經授權不得轉載。